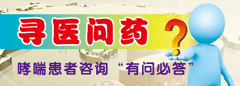白介素-6作为哮喘一种的生物标记物:是炒作还是另有其他?
2017/03/15
理想的生物标志物应该易获得、可再现、敏感且特异,通过呈现患者的反应应答治疗,并被医学界接受。为了满足这些要求,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必须经过一系列长期的研究,包括回顾性和更好的前瞻性研究,多个研究中的一致发现,针对金标准的有效性研究,评估生物标志物对变化敏感性的治疗研究,评估生物标志物提供预后能力的长期研究,以及提供在医学界获得接受所需的生物学/病理学可信性的基础科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哮喘生物标志物是一个特别令人畏惧的挑战,因为哮喘实际上是一种缺乏精确定义并且在其表现和治疗中高度异质的综合征。然而,因为一些哮喘治疗非常昂贵,因此相比效果来说,探索某些生物标志物疾病分级和助集中高成功率治疗方案的能力其所产生的时间/费用是值得的。FeNO最初被称为这样一种生物标志物,但由于肺部协会被炒作所诱惑,其受欢迎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如Gartner炒作周期所示。
白细胞介素(IL)-6是作为促炎介质和急性期反应诱导剂的多效细胞因子,也已被报道具有抗炎性质。尽管主要与T细胞和巨噬细胞相关,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在肺中气道上皮是IL-6的主要来源。在其抗炎作用中,IL-6对肿瘤坏死因子-α和IL-1具有抑制作用。此外,其涉及前列腺素E2的合成。 IL-6是通过固有免疫系统的模式识别受体识别微生物和损伤相关分子模式而产生的。考虑到最近对其在肥胖中作用的兴趣,IL-6也是脂肪细胞的产物并且与公知的全身炎症生物标志物CRP相关。因此,作为在与哮喘密切相关的途径中的主要、关键的细胞信号传导模式,IL-6具有强的生物学可信性。
在疾病中,循环的IL-6在哮喘患者体内、临床哮喘症状活跃的患者其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以及内源性哮喘患者中升高。后者的发现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IL-6评估哮喘患者表型中的作用更一般。 IL-6水平也受到病毒感染和肥胖的影响,分别是引起急性发作和严重程度的两个重要的共同因素。此外,BALF中 IL-6水平与循环的IL-6相关,提示有关联。如我们之前所假设的,IL-6水平可能反映肺的活化状态,特别是气道上皮。最后,许多研究表明痰中IL-6与1秒用力呼气量(FEV1)和FEV1 /用力肺活量以及肥胖相关。总之,IL-6显然具有作为哮喘生物标志物的作用。
在本期“欧洲呼吸杂志”上,ILMARINEN 等人报道了一项数据集,来自正在进行的Seinäjoki哮喘研究中的一项为期12年的随访170例成人发作性哮喘患者。成年发作的哮喘患者通常是女性,没有提示早发性(通常是过敏性)哮喘的病史,并且最重要的是具有不良的预后,特征在于哮喘控制不足和频繁急性加重。这些患者可能相当具有挑战性:医疗债务率高、生理疾病以及生活质量差。 ILMARINEN 等人假设共病的普遍率高可能与全身性炎症或肺炎性状态流入到循环中有关。作者通过高循环浓度CRP和/或IL-6的评估来报道全身炎症的高比率。患多种合并症的患者更可能是体重指数较高、较长吸烟年数、使用更多的吸入性皮质类固醇(ICS)以及哮喘控制和肺功能较差的女性。IL-6浓度显示与CRP呈合理的相关性,并且IL-6也与肺功能相关,尽管很弱。有趣的是,IL-6浓度和嗜酸性粒细胞数是当前ICS剂量的预测因子。作者得出结论:共存病和IL-6浓度预示着哮喘症状和ICS的使用,从而承诺IL-6是潜在有效的生物标志物。
那么这些发现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为了哮喘患者而针对一个有用的生物标志物所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合并症是否是炎症产物溢出到循环中并影响远端部位的结果,或者是否哮喘的严重性是源自其他部位的全身炎症产物负担的结果,例如亚临床感染过程,组织损伤或脂肪组织?最后最重要的是,IL-6是罪魁祸首还是因为它的生物动力学仅仅是过程的标志?
作为哮喘的生物标志物,IL-6具有一些优点,但也有一些缺点。首先,它几乎不具有特异性,并且在其他肺疾病[5]和许多其他非肺疾病中牵连并且升高。此外,在BALF /痰中联系密切、可重复并且容易产生生物学可信性,尤其是在肺功能的损失方面,其中仅仅将IL-6与转化生长因子-β,气道壁中胶原的沉积,以及中枢气道功能的丧失相关联。虽然其他机制可以发挥作用,但目前IL-6评估的最佳作用似乎是作为与肺功能丧失预后相关的疾病活动度或气道损伤的客观量度。考虑到肺功能(其也可以被认为是生物标志物)作用不错,尚不清楚IL-6评估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加入到那些经考验证明好的生物标志物当中。到头来,只有通过阻断其产生、中和蛋白质或用许多可用的治疗剂阻断其受体来控制IL-6 ,我们才开始清楚测量IL- 6的功效。
文献来源:Poynter ME, Irvin CG. Interleukin-6 as a biomarker for asthma: hype or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Eur Respir J. 2016 Oct;48(4):979-981 (IF:8.332)
上一篇:
我们能从哮喘患者的血粒细胞变化模式中学到什么呢?
下一篇:
哮喘和支气管扩张急性加重风险:我们仍需要更多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