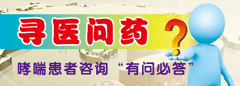气道炎症标志物研究进展及其临床应用
2015/09/24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710032
呼出气一氧化氮
由于呼出气生物标志分析在诊断肺部疾病的潜在应用价值,呼出气分析在临床实践中已引起高度重视。对于哮喘来说,最常用的呼出气指标分析是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检测。该分子于1991年首次在哺乳动物呼出气中被发现,主要来源于气道上皮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和多种炎性细胞。内源性NO由三种一氧化氮合酶(NOS)同功酶催化产生。神经源性NOS(NOS1)和内皮性NOS(NOS3)属组成型合酶,由钙离子激活,产生少量NO,在局部发挥调节作用;而诱导性NOS(NOS2)不依赖于钙离子,在炎症相关因子诱导下表达上调并激活,产生大量NO。NOSs在催化L-精氨酸转变为L-瓜氨酸的同时产生了NO。哮喘患者气道上皮细胞内过表达NOS2,当其接受吸入型糖皮质激素(ICS)治疗后NOS2表达减少。使用NOS2选择性抑制剂可降低哮喘患者和正常人群的FeNO[3]。
所产生的NO与半胱氨酸和谷胱甘肽中的巯基相互作用,生成硫化亚硝基蛋白和硫化亚硝基硫醇,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气道对NO的存储过程。约70-90%的呼出气NO是由硫化亚硝基硫醇所释放,因此认为硫化亚硝基硫醇是机体主要的NO来源。此外,部分呼出气中的NO也来源于硝酸盐形成硝酸——气道酸化过程。呼出气NO可通过化学发光和电化学方法检测。FeNO检测结果可能会受到某些人口特征(如:年龄、体重、性别、种族、吸烟与否及酗酒)等因素的影响[4]。
FeNO水平与气道嗜酸性细胞(Eos)炎症紧密相关,重症哮喘患者FeNO水平显著增高,ICS治疗后则有下降。因此,FeNO可作为预测气道Eos炎症和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的指标。目前认为FeNO低于25ppb表明患者Eos性气道炎和对激素治疗反应的可能性较低。有研究表明,以FeNO指导哮喘孕妇的治疗可减少急性发作[5]。无论成人或是儿童,FeNO还能帮助鉴别过敏性和非过敏性[6,7]。因此,FeNO可能是一种具有广泛运用前景的监测指标。然而,也有阴性结果的报道:认为它在指导哮喘降级治疗时并不优于临床表现和肺功能测定[8]。
呼出气冷凝液生物标志
呼出气冷凝液(EBC)含有许多挥发性和非挥发性炎性介质,检测这些分子有助于医生判断和理解哮喘的病理生理改变。EBC的收集方法简单、无创。将温热的呼出气收集于一个0度冷凝管内,就获得了EBC。然而有关EBC的采集方法和分子检测技术目前尚未规范。当前,对于EBC的检测指标主要有:pH,H2O2,NO,白三烯,异前列素,细胞因子等。
pH:哮喘患者明显高于正常人,经抗炎治疗后可回至正常。低pH反应哮喘的急性发作,与痰液中Eos增多、亚硝酸盐/硝酸盐和氧化应激相关。炎症过程中所产生的挥发酸可使降低EBC的pH。
H2O2是一种氧自由基,与气道内氧化应激有关。哮喘患者显著增高,优其是重症哮喘。吸烟会提高H2O2水平。在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其水平可下降。因此,H2O2或许是检测哮喘控制程度的一种潜在的分子标志[9]。
微小RNA(miRNA)在哮喘患者和正常人群间存在差异。已知大量的Th2相关细胞因子受miRNA的调控。mir-1248调控IL-13,IL-5和IgE高亲和力受体,而 mir-21则可能调控IL-13受体。然而,对其在临床中的意义研究不多。
EBC中包含前列腺素E2(PGE2),血栓素B2(TXB2)、白三烯B4(LTB4)和半胱氨酰白三烯(Cys-LTs)等炎性介质。哮喘患者与正常人群间,PGE2水平无明显差别,且ICS或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治疗对此无明显影响。但是吸烟哮喘患者EBC中PGE2水平较非吸烟哮喘患者高,因此PGE2可用来评估周围环境对气道炎的影响。哮喘患者EBC中TXB2,LTB4、半胱氨酸白三烯等水平升高。然而只有CysLTs在糖皮质激素和孟鲁司特等治疗后回归正常,表明CysLTs可用来预测哮喘患者对激素和白三烯调节剂治疗反应。
异前列腺素是一类前列腺素样化合物总称,反应气道内氧化应激状况。哮喘患者EBC内主要的异列腺素是8-异前列腺素,其水平是正常人的2倍,且随着疾病的加重而逐渐增高[10]。
哮喘发病与气道慢性炎症和过表达Th2细胞因子密切相关。因此,在哮喘气道中发现部分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生长因子(如IL-4,IL-18,IL-17和TNF-α)。由于其浓度低于可测量的最低水平,因此临床应用受限。相信随着更灵敏的检测试剂盒问世,在不久的将来,测量EBC中的细胞因子浓度评估哮喘气道炎症,监测治疗效果会成为可能。
此外,内皮素-1(ET-1)作为一种促炎介质参与哮喘气道高反应性facilitate the detection of disease phenotypes as well as和气道重塑。运动会加速气道上皮产生并释放ET-1。同样,运动也会提升哮喘患者气道灌洗液中腺苷含量。儿童或成人哮喘患者的EBC中eotaxin水平较正常人高。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在哮喘的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Karakoc等研究发现哮喘患者MMP-9水平与其肺功能和IL-4等细胞因子水平呈正相关。但它们在临床中的指导意义如何尚不完全清楚。
诱导痰生物标记
诱导痰检查是一种相对安全、无创的检测方法,国内对此已有规范的操作程序,对提高检查的准确性和安全性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诱导痰液包含沉渣层(含细胞成份,如Eos、中性粒细胞)和上清层(含细胞因子等),这些指标的检测可作为评估哮喘严重性和急性加重的依据。
痰液中Eos计数是反映哮喘严重程度和对激素治疗反应的关键指标。过敏性哮喘患者痰液中Eos较健康人显著增多,与急性发作和气道高反应有关[11]。糖皮质激素治疗可使之降低,但停止治疗后其数量会再次升高。中性粒细胞在重症哮喘(特别是非Eos哮喘)气道炎症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些研究报道重症哮喘患者痰液中中性粒细胞数量显著增多。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数值增幅与痰液中中性粒细胞计数呈负相关[12]。
痰液上清中可检测出部分可溶性介质,包括Eos分泌蛋白、NO衍生物和多种细胞因子等。重症哮喘患者诱导痰液上清中ECP、IL-4、IL-5、IL-13、TNF-α、IL-6、G-CSF、IL-12等。哮喘患者诱导痰液上清中的CysLTs含量升高,LTs受体拮抗剂具有抑制哮喘Eos向炎症部位趋化的功能[13]。此外,哮喘患者痰液中尿激酶和血浆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因子1水平增高。哮喘急性发作时诱导痰中神经激肽A水平也明显增高。哮喘患者诱导痰液的pH值较正常人群偏低,其数值与哮喘的不同病理生理特征相关。
气道重塑是哮喘的特征性改变之一,诱导痰液中的的一些重要介质与之相关联,如前胶原肽,金属基质蛋白酶(MMPs),金属基质蛋白酶组织抑制物(TIMP)及TGF-β等。ICS治疗对痰液中MMP-9的表达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此外,研究显示诱导痰中MMP-9/TIMP1平衡失调,MMP9增多可能是导致胞外基质蛋白沉积的重要原因。ICS治疗后哮喘患者诱导痰中TGF-β水平仍有增高。哮喘急性加重期I型胶原合成增多。以上事实说明ICS不能调节气道重塑介质,但孟鲁司特治疗可使气道内Eos浸润及杯状细胞化生明显减少,肺功能显著改进。此外,研究还显示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能在哮喘气道重塑的治疗上具有一定作用,有研究表明使用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厄洛替尼等药物会减少上皮下胶原沉积、平滑肌厚度和IL-4、IL-5、IL-13、TGF-β和TNF-α等因子含量[14]。
血液生物标志
血清总IgE和抗原特异性IgE水平有助于确定哮喘亚型。血清中总IgE水平与哮喘的严重程度相关。体内抗原特异性IgE是过敏性哮喘的生物标志,目前多采用皮肤点刺法检测。但血清IgE不能预测哮喘治疗效果。有研究报道经糖皮质激素治疗后血清中IL-4水平显著下降,而IL-4的下降会进一步导致哮喘患者血清总IgE和抗原特异性IgE水平的下调[15]。IgE单抗---奥马珠单抗可减少严重哮喘的急性发作次数[16]。
外周血Eos计数与哮喘的严重程度具有一定相关性,因此可将其作为监控哮喘药物治疗效果的一项生物标志。不论是儿童哮喘还是成年哮喘患者,外周血中Eos可能会增多,并且与患者肺功能呈负相关系。儿童重症哮喘患者血清中Eos颗粒蛋白(ECP,EDN等)含量增高。使用激素治疗哮喘后, Eos的发育受到抑制,其数量也会减少。使用IL-5抗体、IgE抗体、白三烯受体拮抗剂、5-酯氧化酶抑制剂可降低患者外周血中Eos数量[17]。
Verrill等鉴定出4中急性时相蛋白(血浆铜蓝蛋白、触珠蛋白、血液结合素及α2巨球蛋白),它们具有重要的抗炎作用。通过双相凝胶电泳技术所作的蛋白质组学分析,证实在哮喘患者体内上述4种蛋白表达均增高。因此,利用生物分子组合可以提高对哮喘诊断的预测能力,有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18]。
Yamamoto等观察了哮喘患者经吸入抗原激发后外周血中miRNA的变化情况,发现哮喘患者在吸入抗原激发后,其体内mir-192明显低于抗原激发前和正常者,提示mir-192涉及哮喘发病[19]。
血清IL-3,IL-18,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肝细胞生长因子和干细胞生长因子β表达水平在未控制患者明显高于控制良好者和健康对照者。研究发现,Th17细胞亚群在过敏性哮喘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IL-23是调控Th17分化的重要细胞因子。在哮喘儿童体内IL-23表达水平较高,且与肺功能呈负相关性。Eos分泌的骨桥蛋白(OPN)是一种多功能细胞因子,与气道过敏性反应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哮喘患者体内具有较高水平的OPN,然而,其浓度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并无相关性[20]。T细胞表达和分泌的RANTES是一种关键趋化因子,在重症哮喘患者表达水平增高。血清中RANTES水平与Eos计数、血清总IgE相关,并与患者FEV1呈负相关[21]。
骨膜蛋白是Th2细胞诱导哮喘的一种重要生物标志,可诱导大量嗜酸性粒细胞聚集于气道组织,受IL-13调控。血清中骨膜蛋白较血清中Ig-E和Eos数量能更好地反映气道Eos炎症[22]。
壳多糖酶样蛋白YKL-40也涉及哮喘等多种炎性疾病的发病过程。然而,其与IgE、病情严重程度、急性发作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尚没有一致结果。
共刺激因子OX40及其配体参与嗜酸性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的产生。哮喘患儿血清中OX40L的表达水平随着疾病的急性加重而升高[23]。
血清中瘦素水平和体质指数与儿童哮喘严重程度呈正相关[24]。
尿液生物标记物
LTC4,LTD4和LTE4均通过花生四烯酸5-酯氧化酶途径合成。LTC4是肺组织中花生四烯酸的主要代谢产物,其结构极不稳定,会快速代谢为LTD4及LTE4,而LTD4及LTE4结构较为稳定,最终随尿液排出。不论是成年哮喘患者还是儿童患儿,其尿液中LTE4含量较正常人群显著长升高,并与哮喘的严重程度、急性加重、过敏原激发等相关[25,26]。不耐受阿司匹林的哮喘患者尿液中LTE4含量较耐受阿司匹林的哮喘患者高[27]。虽然ICS治疗对于大多数哮喘患者有效,但ICS对于尿液中LTE4含量无明影响[28]。
哮喘患者尿液中可检测出Eos分泌的嗜酸性细胞蛋白X(EPX)或EDN。儿童哮喘患者尿液EPX浓度随着疾病的急性加重而增升高,随着有效的抗炎治疗,其浓度逐渐降低。Nuijsink等研究了尿液中EPX与气道Eos炎症的相关性,得出uEPX与FEV1及诱导痰液中嗜酸性粒细胞数量具有相关性[29]。
前列腺素D2(PGD2)是细胞内环氧化酶通路的主要代谢产物,具有强力收缩支气管以及舒张血管效应,因此它在哮喘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人体肺部肥大细胞是PGD2的主要来源,PGD2随后代谢为9α,11β-PGF2,经尿液快速排出。许多研究证实在经抗原或阿斯匹林激发后哮喘患者尿内9α,11β-PGF2水平增高。同样,在哮喘急性发作的儿童或运动诱发哮喘患者尿内9α,11β-PGF2水平也会增高。然而,尿液中9α,11β-PGF2水平对判断哮喘严重程度价值有限。糖皮质激素能减少哮喘肺组织中Eos和肥大细胞数量,因此间接降低尿液PDG2含量。
3-溴酪氨酸(BrTyr)是Eos参与产生的一种蛋白氧化产物。活化的Eos释放颗粒蛋白和H2O2,H2O2在Eos过氧化物酶的催化下使溴化物发生氧化反应转变为溴化氧化物。溴化氧化物损伤组织蛋白进而引起酪氨酸残基的再次溴化,形成3-BrTyr和3,5-二溴酪氨酸。这些溴化的酪氨酸随尿液排出,因此检测尿液中含量可作为监测哮喘控制水平和预测急性发作的一种无创技术,对儿童患者更为合适。哮喘患者中尿液中BrTyr水平显著增高,急性加重时增高更为明显,并与气流受限参数相关[30]。
生物标志物的分析对哮喘表型的识别和个体化治疗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在上述标志中有的已在临床应用并取得很好的指导作用,然而大部分标志物的临床意义未完全明了,尚需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证实。相信随着检测仪器的改进、操作方法的进一步规范,将会有更多更有意义的生物标志被筛选出来。
参考文献
1.Fahy JV. Eosinophilic and neutrophilic inflammation in asthma: insights from clinical studies. Proc. Am. Thorac. Soc.2009; 6: 256–9.
2.Taylor DR. Biomarkers of inflammation in asthma: a clinical perspective. Semin.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2; 33: 620–9.
3.Brindicci C, Ito K, Barnes PJ, Kharitonov SA. Effect of an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hibitor on differential flow-exhaled nitric oxide in asthmatic patients and healthy volunteers. Chest 2007; 132: 581–8.
4.Dressel H, de la Motte D, Reichert J, et al.. Exhaled nitric oxide: independent effects of atopy, smoking,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gender and height. Respir.Med. 2008; 102: 962–9.
5.Powell H, Murphy VE, Taylor DR, et al.Management of asthma in pregnancy guided by measurement of fraction of exhaled nitric oxide: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11; 378: 983–90.
6.Hervas D,Milan JM, Garde J. Differences in exhaled nitric oxide in atopic children. Allergol. Immunopathol. (Madr) 2008; 36: 331–5.
7. Scott M, Raza A, Karmaus W, et al. Influence of atopy and asthma on exhaled nitric oxide in an unselected birth cohort study. Thorax 2010; 65: 258–62.
上一篇:
抗IgE治疗过敏性哮喘的长期有效性、安全性和成本效益分析
下一篇:
哮喘气道重塑的发生机制和治疗对策